千千分享|斯坦福哲学百科词条选(一)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Reproduction and the Family”这一斯坦福哲学百科(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词条的第一部分论述了为什么家庭应当由公权力介入、以正义原则进行约束。
第二部分,它还简述了两种用于评估家庭正义的核心价值:个人选择自由与平等。个人选择自由应当被尊重,自愿缔结的婚姻可以说是正义的。但如果个人自愿进入一段权力关系不对等的婚姻,这是否还是正义的呢?又或者说,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自愿”是真正的自愿吗?我们可以在这一词条的第二部分找到思考这些问题的方式。
最后,词条的第三部分讨论了女性主义哲学家对堕胎权与商业代孕的看法,“堕胎是个人选择自由”是支持堕胎权的充分理由吗?代孕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分别有什么样的理由?尽管在我国,堕胎与代孕问题在法律上并不存在争议,但了解西方学者如何从道德角度来讨论这两个问题仍旧有益。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之所以组织编译这篇外文文献,是因为我们认为,作为推动性别平等进程的工作者,只有对我们所秉持的信念有了更深入、更清晰的理解后,才能够更坚定地倡导我们所信奉的价值。


来源: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Reproduction and the Family”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feminism-family/)
首次发表日期:2004年11月6日
实质性修订日期:2013年10月21日
1. 为什么家庭应遵循正义原则?
1.1 家庭是一种政治制度
1.2 家庭影响未来公民的培养
1.3 家庭抑制或促进女性的自由
2.如何评估家庭结构?
2.1 基于选择的评估
2.2 基于平等的评估
2.3 儿童的利益
3. 生育选择
3.1 堕胎
3.2 商业代孕
4. 结论
历史上,许多捍卫公共政治领域正义的哲学家并不主张家庭结构的正义。相反,大多数人认为家庭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应当免受国家干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被划分为两个互不相干的空间,后者被认为不受公共行为的约束。这些哲学家并不将家庭中的私人权力正当化,而仅仅是对其视而不见。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是一个例外。他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中指出,若女性在家庭中没有平等地位,那么女性也难以在社会中实现平等。他提到,在男权主导的家庭中成长的男孩可能会滋长“自我崇拜、不公平的自我优越感”,认为“仅凭男性身份便天然优越于全人类中一半的人”。这样的男孩长大后,如何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女性?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继承并深化了对视家庭为私人领域观念的批判。实际上,“个人的即政治的”(即家庭也是政治的一部分)这一思想,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核心理念。


女性主义者认为,家庭、性别与生育等所谓的私人领域,必须纳入政治范畴,并受正义原则的约束,原因有三:
1. 家庭不是“自然”的秩序,而是由法律支持的社会制度。例如,婚姻是一种社会制度。因此,国家必须干预家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干预以及基于什么原则进行干预。
2. 国家在未来公民的发展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
3. 传统家庭中的劳动分工限制了女性在社会中的机会和自由。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三条论点。
1.1 家庭是一种政治制度
传统观点通常将家庭视为前政治或非政治的机构。认为家庭是前政治的观点将家庭的基础视为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某些事实,认为其基础是自然属性。认为家庭是非政治的观点则指出,家庭中不存在政治的基本特征,如资源稀缺、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这两种假设都存在问题,受到了女性主义者的批评。
1.1.1 为什么家庭不是前政治的
许多传统家庭理论家认为,自然决定了家庭内的任务分工。女性天生希望拥有并养育孩子;男性则天生没有这种意愿(Rousseau 1762)。因此,性别差异在生理上有其基础:女性在养育子女和家庭劳动上的主导角色是她们的生物学命运。
对此,女性主义者提出了三种回应:
l 社会建构论者(Social constructivists)否认男性与女性在身体或心理上的本质差异能够解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Haslanger 2000)。她们认为,文化与社会塑造了看似 “自然” 的性别差异,许多被认为是性别不平等根源的男女差异,应该被视为这种不平等的结果。例如, 主张,性别间身高与体力的差异受到饮食、劳动分工和身体训练的影响。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试图证明文化、宗教和社会阶级在塑造女性生活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Scott 1988)。
l 差异女性主义者(Difference feminists)接受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某些生理或心理差异,但质疑这些差异的规范性和社会意义。她们认为,即使女性天生更有养育性或更注重人际关系,这些特性是否重要取决于社会如何评价它们(Gilligan 1982, Noddings 1986)。例如,如果养育更被社会所看重,那么我们可能会可能会重新安排工作世界,使女性(和男性)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或者,我们可能会为女性(和男性)的家庭劳动以及抚养孩子支付报酬。差异女性主义者试图赞美并重新评估那些与女性相关的传统特征。在她们看来,性别分工本身并非必然存在问题,只要分工是自愿的,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也被恰当评价。这种差异视角或许最能通过一句熟悉的俏皮话来概括:没有野心的女人才只想和男性变得平等(women who want to be equal with men lack ambition.)。
l 反压迫(anti-subordination)女性主义视角则不将生物学和心理学差异视作家庭和生育问题的辩论焦点。将男女的“差异”与“平等”狭隘地对立起来,掩盖了平等待人的核心。即使男女之间确实存在一些自然差异,关键在于,这些差异不能为那些使女性容易陷入贫困、同工不同酬和家庭暴力的社会结构提供正当理由。她们强调,不论女性的生物学或心理学事实如何,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女性就应当在社会中处于从属位置(MacKinnon 1989,Rhode 1989)。生物学不能解释夫妻法律人格同一原则(the doctrine of coverture)——在18世纪,妻子的财产与权利为丈夫的一部分——也不能解释现代有关离婚、孩子抚养权及女性生育的法律。我们的自然本性推不出工作与学校的时间安排,这一安排使得任何人都极其难以平衡工作与养育孩子。尽管自然本性是性别差异的一个原因,它本身也解释不了性别不平等,更不能使性别不平等正当化。
1.1.2 为什么家庭不是非政治的
当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洞见是,法律已经渗透到了家庭中,正如夫妻法律人格同一原则那样。通过强制与社会习惯,家庭一直为法律所塑造。例如,在美国,各州法律规定了谁可以结婚,谁有亲权,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离婚,以及谁可以继承遗产。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禁止同性伴侣结婚的法律,在许多国家,同性伴侣不被允许收养孩子;在其他国家,女儿被禁止继承财产,这使她们难以过上好生活。因此,家庭实际上始终受到国家的深度干预,而这些干预往往不利于女性的平等(Fineman 1995)。
尽管如此,有些政治思想家仍旧认为,在家庭中运用法律进行权利义务分配是不恰当的。虽然家庭可以作为一个法律实体,通过婚姻制度进行恰当的监管,但这些思想家认为,家庭日常互动应当基于不同的原则。家庭的基础是爱与情感,而非正义。适用正义的一些情况,如利益冲突、权力及资源稀缺,并不存在于家庭中,至少并不存在于运转良好的家庭中。这些思想家批评将正义引入家庭的观点,他们不认为洗碗这类事务应当由正义原则进行分配(Sandel 1982)。
值得一提的是,家庭有时承载了这样一种理想:它是超越正义的联合体,它的成员从各自交织的共同生活、共同善出发来思考问题。用Christopher Lasch的话来说,这样的家庭是“残酷世界中的避风港”。但这种对家庭的看法在一些方面存在严重的局限性。首先,许多家庭并非基于爱与自愿,而是基于强制。真实的家庭往往充满分歧,极端情况下甚至伴随暴力。在这些家庭中,融入正义规范将能够改善家庭的情况。其次,即使在充满爱的家庭中,女性也因家庭中劳动分工的不平等,承担育儿和家务责任而处于更脆弱的处境。虽然理想家庭中的成员关系可能超越了正义,但对公民来说,反思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了社会正义与家庭生活仍旧是恰当的。我们大多数既是家庭成员,也是一个更大政治体的成员:没有理由认为基于和谐情感的视角不能与基于正义标准的视角并存(Okin 1989)。最后,这两种视角不同又互补,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公民会试图将正义原则应用于洗碗。
然而,必须用正义治理家庭,其原因并不仅仅是现实中的家庭远非理想。由于家庭会对未来的公民、女性的机会与真正的自由产生影响,国家因此能从维护并促进正义的家庭中获益,这也是必须用正义治理家庭的原因。
1.2 家庭影响未来公民的培养
在我们的社会,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从某种形式的家庭中开始的。一个人所成长的家庭类型会直接影响他们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家庭中,儿童首先接触到关于“对”与“错”的概念,并通过成年人的行为榜样塑造自己对可能性和未来的认知。家庭是重要的道德学习场所,但遗憾的是,许多家庭教育孩子的不是正义原则,而是服从与从属的观念。在密尔之后,女性主义学者质疑,如果孩子在家庭中首次体验到的互动是“不平等的利他主义、支配和操控”,他们如何能够学会并接受一个尊崇人人平等的民主社会所必需的正义原则(Okin 1989)。
柏拉图(Plato)也认识到家庭对于个体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家庭能够促进或抑制儿童的天赋和能力。在《理想国》(the Republic)第五卷中,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当正义理论家充分考虑家庭对儿童潜能发展深远且往往不公平的影响时,他们将不得不得出家庭必须要被废除的结论。尽管很少有女性主义者像柏拉图一样提议废除家庭,但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家庭需要改革。
家庭不仅是道德学习的场所,更是孩子成长中的重要支持系统。父母在照顾未成年子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国家需要规范家庭,以确保所有儿童都受到教育,接种预防传染病的疫苗,并满足其基本需求。所有国家都会关心儿童长大后是否有文化,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因此,所有国家都为儿童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公费教育。国家至少也部分地依赖于家庭中的照护与养育工作,而这项工作迄今为止主要由女性承担。家务劳动是如此重要,但为什么它没有获得更多的公众认可?女性主义者强有力地论证了认真对待家庭中的照护劳动的必要性,并呼吁国家关注照护劳动中涉及的正义问题(Kittay 1999)。女性主义者还主张,正义的国家必须提供(一种公共的)照顾,以确保所有儿童,包括男孩和女孩、富人和穷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平等的机会,在长大后能够参与社会。
1.3 家庭抑制或促进女性的自由
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在20世纪后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大多数家庭仍以不平等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女性仍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不仅包括维持家庭,还包括养育和照料子女。女性主义学者批判了那些掩盖这一不平等现象的传统家庭观。例如,她们批评主流经济学对家庭的分析,这种分析将一家之主视为能够无私地代表所有家庭成员利益的人(参见 Becker 1981)。研究表明,在贫困国家,当发展援助给予家庭中男性而非女性主人时,用于子女照料的资金比例会显著减少(Haddad et al. 1997)。
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表明了女性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如何限制了她们对事业的追求以及工作上的竞争力(Bergmann 1986, Folbre 1994)。因此,许多妇女在经济上仍然依赖其男性伴侣,在离婚时更容易陷入贫困。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显示,离婚后的一年内,男性的生活水平平均提高了42%,而女性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78% (Weitzman 1985)。这种收入和财富的巨大差异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其中之一是,全身心投入抚养孩子的女性比丈夫通常更难以满足工作所需的资质,其工作经验也更缺乏。
女性的经济依赖性反过来又使她们更容易受到丈夫或其他男性伴侣的身体、性或心理方面的虐待(Gordon, 1988;Global Fund for Women Report 1992)。女性退出婚姻的能力是不对等的,这使得丈夫/男性伴侣在婚姻中占据权力上位,有更多谈判优势(Sen 1989)。
为现状辩护的人经常主张,如果女性的机会比男性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们自己的选择。女性主义者反驳了这一观点,她们指出这些选择受到外部环境的塑造和限制,而这些限制本身是不合理的,也并非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一些女性主义者遵循Nancy Chodorow(1978)的观点,认为儿童的主要养育者是母亲这一事实,导致了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性别分化的发展路径。女孩认同同性父母的养育方式,感觉与他人的联系更紧,而男孩则因认同缺席的父亲而感到更为“个体化”。Chodorow 认为,母职(mothering)通过一种基本无意识的机制代代相传,而这种机制又延续了女性在家庭和工作中的不平等。
Chodorow的研究是有争议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女孩和男孩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着对他们行为举止的不同期待。孩子们从父母、老师、同龄人和媒体那里接受到强烈的带有文化意涵的信息,这些信息告诉孩子们什么是对于其性别来说恰当的特质和行为。女孩被认为应该是有爱心的、自我牺牲的、没有攻击性的、有吸引力的;“照护”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女性的特征。传统上,这些特质导致了女性的不平等:养育者不被视为优秀的领导者。很少有女性首席执行官、将军或政治领导人。女孩也可能因未来会结婚和养育子女而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她们比男孩更不可能投资于自己的人力“资本”。
第二种女性主义回应强调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选择如何与家庭外的不公社会结构交互作用,特别是与经济中的性别隔离劳动分工相作用。在这种分工中,女性从事相同工作的收入通常仅为男性的75%。鉴于女性的收入较低,对于必须自行承担育儿责任的家庭来说,让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理性选择”。但一旦女性退出职场,她们的技能发展和收入能力都会进一步落后于男性。育儿是一个耗时巨大的任务,那些单独承担育儿责任的人几乎不可能追求诸如教育、政治职位或高难度职业等其他目标。工作和家庭的结构因此形成了一个“脆弱性循环”,限制了妇女的生活和选择(Okin 1989)。即便那些试图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的女性,也面临着许多障碍,包括缺乏高质量、政府资助的日托服务,无法灵活调整的工作安排以应对生病的孩子,似乎默认家庭中有专职家长的学校时间安排,以及她们仍被期望完成“第二份工”(Hochschild 1989),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的责任。统计分析表明,当母亲往往会降低妇女的收入,即使她没有暂停工作(Folbre 1994)。性别不平等在经济和政府的高层职位中依然普遍存在:白人男性约占人口的40%,但却占据了95%的高层管理职位、90%的报纸编辑职位和80%的国会立法者职位(Rhode 1997)。尽管相较于过去来说,女性能够获得一些经济和政府精英职位,但有证据表明这一进展已趋于停滞(Correll 2004)。
女性主义者一致认为,当代家庭不仅是选择的领域,也是约束的领域。女性主义者也普遍认同,社会中的性别等级制度是不公平的,尽管对于其根源存在不同看法。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家庭是性别不公正的“支点”(Okin 1989);而其他人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工作和机会的结构(Bergmann 1986);还有一些人强调性宰制和性暴力(MacKinnon 1989)。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性别不平等有重要影响,显然难以将它们完全归结为某个单一原因。因此,深入理解这些不同来源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很明显,这是奥金(Okin 1989)所说的“脆弱性循环”,通过这种循环,女性在家庭中的不平等地位与女性在工作场所的不平等地位相互作用。例如,由于女性的收入通常低于男性,当家庭中有人需要退出职场以抚养孩子时,经济上更合理的选择往往是让收入较低的女性退出。此外,性别显然还与种族和阶级等其他社会不利因素交互影响。近年来,女性主义对家庭的研究日益关注女性在多样化家庭形式中的不同经验。这些家庭形式不仅包括异性恋的双亲家庭,还包括单身女性、同性恋家庭以及贫困家庭。在研究时,我们必须谨慎对待不同的社会现象,而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尽管在本文中有时会使用“家庭”这一术语,但务必要牢记家庭形式和情境的多样性。
无论家庭是性别不公的主要原因,还是与其他社会结构和文化预期共同作用的因素,女性主义者都指出,家庭是女性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再生产体系的一部分。不能脱离这一体系孤立地看待家庭,也不能假定家庭本身就是公正的,因为显然许多家庭并非如此。对女性主义者来说,问题不在于国家是否可以干预家庭和生育,而在于如何干预,以及干预的目的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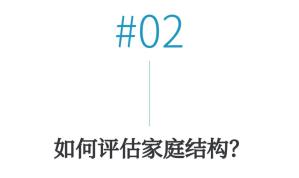

如何评估家庭结构?如何分配育儿和家务责任?谁有权决定家庭收入的分配?谁有权组成家庭?谁有权生育?什么定义了“父母”?一个孩子可以有多少父母?一个父母可以有多少孩子?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技术为人类提供了多种成为父母的方式。
以下,我们将探讨两种核心价值:个人选择与平等,女性主义者主张这两种价值应指导我们如何构建家庭。
2.1 基于选择的评估
传统家庭在过去50年里经历了许多变化。二战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劳动力市场。离婚率显著上升:1980年代的离婚率是1940年的2.5倍。避孕药的发展使女性能够更轻松地避免意外怀孕并规划生育时间。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以及扩展家庭(译者注:extended family,扩展家庭,即除了核心家庭之外,还包括其他亲戚成员的家庭形式。)的数量不断增加。到1989年,美国25%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中,其中许多家庭处于贫困状态,社会普遍感到传统家庭模式陷入了危机(Minow 1997)。经济、技术和社会因素共同使全职家庭主妇,妻子在家带孩子、丈夫外出工作这一传统家庭模式的数量减少。
家庭相关的法律也发生了变化。现代法律更倾向于将男性和女性视为平等的个体,只有在彼此自愿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相互之间的支配或控制关系。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婚姻、离婚和堕胎的法律限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之间相继放宽。例如,在Loving v. Virginia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禁止跨种族婚姻的州法律;在罗伊诉韦德(Roe v Wade)一案中,堕胎被合法化(译者注:该案目前已于2022年被推翻)。当然,这些变化也伴随着争议,女性在生育选择方面仍面临严重限制。同样,同性恋者通常也无法结婚,尽管相关法律和规范正在朝着支持同性婚姻的方向发展(例如最近的Hollingsworth v. Perry和United States v. Windsor案)。家庭逐渐从一种基于固定身份的等级制度,逐步演变为一种基于契约的个人关系。许多人现在将婚姻视为一种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调整条款的合同,而非一种不可更改的状态。
契约婚姻的理念应扩展到什么程度?一些女性主义者提议扩大契约模型,允许任何有自愿能力的成年人结婚,并自由选择他们之间关系的条款。这些女性主义者主张彻底废除由国家定义的婚姻,让每对想要结婚的伴侣自行签订契约(Fineman 1995;Weitzman 1985)。实际上,契约婚姻不仅允许同性伴侣结婚,还允许多偶制婚姻。
基于契约或选择的女性主义者主张让个人自主决定他们希望创造的家庭类型。因此,他们主张人们不受国家限制,自由达成就生育问题达成一致,包括堕胎和避孕的权利,转让亲权的权利以及买卖精子、卵子和代孕服务的权利。因此,选择主义的女性主义者(choice feminists)会允许同性伴侣、不孕夫妇或单身人士在怀孕前,根据他们自己决定的条款,签订获取精子、卵子或代孕服务的契约。
从契约的视角来看,传统主义者关于家庭面临“危机”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真正陷入危机的是基于异性恋婚姻的核心家庭。但这种家庭形式从未对女性有利(Coontz 1992)。契约婚姻的倡导者认为,通过扩大选择在生育和我们自己创造的家庭中的作用,女性将得到赋权。例如,契约可以促成新形式的家庭,使同性伴侣、单身女性和男性能够拥有孩子。同性恋家庭在家务分工上通常比异性恋家庭更平等,也更不可能按照性别延续母职角色。另一些人认为,允许女性出售生育服务将释放新的经济力量,从而赋予女性权力并提高她们的福祉(Shalev 1989)。
与家庭拥有超越正义的内在性质这一理想相对立,一些女性主义者甚至建议使用婚姻契约来确定家务分工。她们认为,将婚姻从一种隐含的、基于身份的父权制度转变为一种明确的契约,将增强女性的自由和平等(Weitzman 1985)。这种提议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首先,它未能关注不平等背景会导致契约谈判中权力的不平等(Sen 1989);其次,它可能破坏婚姻中的亲密关系和承诺(Anderson 1993);最后,由于国家需要执行此类契约,它可能导致对家庭生活专制的干涉(Elshtain 1990)。
其他女性主义者批评将选择理念应用于生育和婚姻本身的合理性。她们认为,选择卖淫、代孕或进入性别化(gendered)婚姻之类的行为看似是女性自由选择的,但这些选择实际上基于一些对女性的负面看法,如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或居家好帮手。例如,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 1989)认为,这种选择同样可以被视为建立在从属与宰制之上,而非自由同意之上。类似地,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 1983)质疑所谓女性选择从事卖淫背后的动机。
这些批评对基于选择的婚姻构成多大的挑战?选择观点的支持者可能合理地辩称,如果男女双方能够明确界定彼此关系的条款,并在条款未得到履行时保留退出权,那么至少极端形式的性别压迫将被削弱。他们还可能强调,这种观点能够容纳对人类关系的多样化理解:允许实验性的关系、多元关系和退出选项。契约确实允许男女签订传统性别化的家庭契约,但如果他们是自愿选择的,且表达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我们为何要反对这样的家庭呢?这场争论背后是一个重要的分歧:一个公正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包容不同的家庭关系。男性和女性角色等级化到什么程度超出了社会的容忍边界?一种家庭形式不平等到什么程度才应当被排除在容忍边界之外?
2.2 基于平等的评估
许多平等主义的论点与基于选择的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认为选择、自由和隐私是在家庭和生育中实现正义的重要元素。然而,持这些观点的女性主义者质疑,基于契约和选择的方式是否足以囊括其他的重要价值。某种安排是自愿选择的,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公正的。除了选择,平等主义女性主义者还强调性别平等和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为例。结合上述关于劳动力市场隔离的讨论,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即便家庭中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是自愿选择的,但它仍然在一个不公正的背景结构中运行。因此,即使(假设)是自愿选择的,也不能因此合理化这种分工。对于道德评估而言,选择并非唯一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
首先,为了维护社会正义的背景结构,我们必须警惕可能破坏这些结构的选择。如果性别化的家庭鼓励女孩的服从和依附,并导致男孩和女孩的机会不平等,那么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努力纠正这些后果。
其次,将婚姻理解为一种选择无法让人关注作为背景的社会制度,女性主义者主张这些制度往往是不公正的。仅仅允许人们选择是不够的,因为人们的选择受到不平等的家庭和工作场所结构、不公平的同工同酬制度以及不足的社会福利的限制,这些因素使许多女性陷入脆弱境地。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密尔就指出,考虑到女性的低工资、就业机会的缺乏以及教育前景的黯淡,女性的婚姻选择几乎不能被称为“自由”。他认为,这种选择更像是一种霍布森选择(Hobson’s choice),即“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但目前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婚姻在经济上依然是必需品。因此,我们必须关注这些选择背后的更广泛的社会背景。
平等主义者补充并限制了基于契约的视角,尤其是在契约使女性陷入从属地位或极端脆弱的情况下。她们还可能对选择视角提出这样的批评:有些选择并非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甚至完全知情是不可能的。例如,基于契约的婚姻和生育观点要求人们完全对其选择结果负责,然而,婚姻和生育契约通常涉及潜在的长期承诺,其影响难以提前预见。例如,一个从未怀过孕的女性能否准确预知放弃对子女的亲权的后果?一名18岁的女性同意在婚姻中实行传统性别化劳动分工,但她能否预见自己在50岁时被丈夫抛弃后的感受?
女性主义者在是否应尊重家庭内部那些破坏性别平等的选择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即便一致认为这些选择需要纠正,她们也对如何处理存在分歧。一些女性主义者倾向于通过间接手段削弱此类选择,包括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人们采取符合公正社会结构的行为,或通过外部措施平衡个体行为的影响。例如,奥金(1989)认为,配偶应平等地享有彼此收入的权利,所有家庭都应享有普惠的托儿服务,工作制度应更加灵活。她主张,通过重塑外部社会结构,是影响家庭内个体选择最适当的方式。相比之下,另一些观点对家庭内的个体选择留有更少的空间。例如,有人建议通过法律强制分担家务责任。但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补救措施可能比其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加糟糕(Elshtain 1990)。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尝试结合并平衡对选择与平等的承诺。Molly Shanley(2003)提出了一种“平等地位”婚姻观,将婚姻作为制度的公共重要性与其对选择自由的扩展相结合,从而将因从属地位或污名化而被剥夺婚姻地位的群体纳入婚姻的范围。Shanley 强调维持正义的婚姻会带来的公共利益,以及在贫困或疾病背景下维持某些家庭关系的利益。平等地位要求关注个体选择的社会背景,特别是贫困、工作场所的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隔离的问题。同时,它也重视亲密关系的价值以及选择在促进或削弱亲密关系中的作用。
基于选择的观点与基于平等的观点在允许的婚姻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尽管基于选择的契约视角支持多偶制婚姻,但平等主义观点并不直接导向应将一夫多妻制合法化。对于平等主义者而言,关键问题是多偶制婚姻是否可能在不导致女性从属地位的情况下实现。
因此,无论是女性主义者还是非女性主义者,都在如何平衡自由和平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在结社自由、宗教自由与性别平等之间。这一分歧影响了国家能正当干预家庭生活的范围。(关于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Nussbaum 2000)
2.3 儿童的利益
尽管有些家庭不能或选择不生育,但在讨论家庭和生育问题时,不可能忽视儿童的利益。考虑到儿童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具体地思考我们所提倡的价值的意义和影响。
以支持契约家庭的选择论点为例。儿童并未选择加入家庭,并且儿童至少在早期需要完全依赖其监护人。父母照顾子女的义务并非基于子女的同意或契约。此外,父母选择建立性别化家庭会直接影响子女的生活,这种选择往往会给子女带来不平等的机会,而这些不平等并非由子女自己选择的。
尽管有些思想家曾提议将父母作为一种需要许可的资格(Mill 1869;LaFollette 1980),但现在任何能够生育子女的人都可以成为父母。(当超过两个人参与子女的生育时,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收养则受到严格的法律监管,但一旦完成收养,在子女抚养方面,法律会平等对待生物学父母和非生物学父母。社会在孩子的养育上给予家庭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只有在孩子遭受虐待或家庭破裂时才会进行干预。
早期,法院在此类案件中采用“最佳利益”标准来决定监护权归属。但这一标准受到了强烈批评:通情达理的人会对何为 “最佳”产生分歧,“最佳”的标准也容易受到阶级、种族和性取向偏见的影响。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 1999)主张采用“基本利益”标准来规范国家的干预。他认为,“基本利益”可以被视为定义一个底线——任何儿童的生活状况都不应低于这条底线。对女性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性别平等是否应被视为儿童的基本利益,如果是,那么如何以最佳方式推动这一目标。
女性主义者已经开始探讨围绕收养和亲权的性别问题,包括未婚父亲是否应拥有母亲送养孩子的否决权,以及妊娠和基因在决定亲权中的作用(Shanley 2001)。
在考虑儿童问题时,我们也必须思考他们是如何被生育的。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根本上源于她们在生育中的角色:在这一观点看来,只有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才能实现女性的平等(Firestone 1970)。然而,这种观点显得过于夸张:使女性从属地位的并非是生育的生物因素,而是其社会和经济背景。显然,养母与生母在面对职场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时同样脆弱。然而,如果生育发生在缺乏社会支持、工作结构僵化的背景下,女性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研究人员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母职惩罚”(motherhood penalty)现象:抚养孩子的女性在薪资和职位上不如同行的未婚女性。美国的《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朝着弥补育儿成本的方向迈出了正确的一步,它为新手父母提供了12周的无薪休假,同时保留福利和返回同等工作岗位的权利。然而,该法案执行起来非常困难,工作氛围使人难以行使这一权利。尤其是男性,更不太可能在子女出生后请假。因此,探讨新的技术,看看它们如何创造新的生育(或不生育)方式是值得的。这些技术对女性的处境有什么影响?对孩子呢?


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男性通过控制女性的性行为和生育,曾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女性身体的主导权。
3.1 堕胎
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以隐含的基本隐私权为基础,赋予女性终止意外怀孕的权利。尽管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指出,这一权利并非绝对,它必须与其他相竞争的利益进行权衡,包括保护孕产妇安全与保护胎儿生命,但该判决依然保护了女性怀孕前三个月期间的堕胎权。然而,在罗伊案之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判决的影响被削弱,它明显体现在:要求通知配偶或父母并取得同意、制定“等待期”以及限制使用公共资金。由于社会争议不断持续,发生针对堕胎服务提供者的暴力和骚扰,愿意并能够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生数量在不断减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85%的县没有堕胎服务机构,还出现两个州只有一家机构提供堕胎服务的情况(Rhode 1997)。此外,很多州甚至已经将晚期堕胎列为刑事犯罪。
尽管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公开支持关于堕胎的某些权利,但堕胎问题无法简单地被归结为男性与女性利益的对立。女性存在于堕胎问题的两方阵营中,她们可能是领袖、活动家和支持者。即使在支持堕胎的女性主义者中,其理由也呈现出着多样化。
一些支持堕胎的论点建立在剥夺胎儿权利的基础之上。他们认为,只有人才享有权利,而胎儿尚未被视为独立的个体(Tooley 1972)。然而,尽管有许多反对堕胎的论点都基于胎儿享有生命权,但并非所有支持合法堕胎的的观点都否认这种权利。朱迪斯·贾维斯·汤姆逊(Judith Jarvis Thomson 1971)的论点指出,即便胎儿被视为具有生命权,国家也不能强迫怀胎的女性作出某些行为。如果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享有自主权,那么她也有权利不让别人以违背她们意愿的方式使用她们的身体。国家无权强迫某人将自己的身体捐献给另一个人,即使那个人急需。(在汤姆逊的著名实验中,一个人的身体与一位著名小提琴家的身体连接在一起,如果她切断她的身体对小提琴家的支持,这位小提琴家就会死去。尽管保持连接可能是一种美德,但汤姆森认为它并不是一种道德要求。)汤姆逊的论点强调身体的完整性和自主性,认为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前提,我们只能允许胎儿在女性的同意之下适用女性的身体。汤姆逊的观点也隐含着性别平等的观点:既然即使是在急需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也不会强迫人们(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将自己的身体捐献给他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只强迫女性是合理的呢?
对于一些女性主义者而言,汤姆逊的类比并不恰当。她们拒绝将胎儿和母亲视作两个独立的个体,而是强调她们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另一些人则担心,如果将堕胎权看作与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关,则可能失去对一些堕胎行为进行质疑的基础。例如,在一些重男轻女现象严重的国家,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行为变得越来越普遍,还有基于度假等琐碎的理由而选择堕胎的行为,这些行为都会因此而变得难以质疑。
将堕胎仅仅视为个人选择自由,或视为权利冲突,忽视了许多其他相关的考量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女性是唯一能怀孕并生育孩子的群体,女性的收入低于男性,她们遭受性暴力,几乎无法获得公共托儿服务,还在家庭或政治决策中拥有比男性更少的权力。堕胎与许多需要考虑的其他问题相关,特别是意外怀孕对女性和孩子生活的影响(Sherwin 1987)。
认为堕胎涉及多种价值的女性主义者,往往比持有单一价值的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妥协。例如,Shrage(1994)提出,考虑到堕胎争议中涉及的价值的多样性,包括生命神圣性(Dworkin 1993)和母亲身份的意义(Luker 1984),我们只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寻求有条件的堕胎,并倡导有助于减少堕胎需求的政策,如容易采取的避孕措施。
3.2 商业代孕
当前,个人或者夫妻都可以就生育服务进行交易。孩子出生,但其基因既不来自生下他们的人,也不来自抚养他们的人,现代技术使这些成为可能。例如,一对夫妻可以购买捐卵者的卵子,将其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或通过人工授精使代孕母亲怀孕。
当然,有关遗传物质的市场交易并不新鲜:在美国,男性出售精子已有数十年。但是,当代法律在商业代孕问题上依旧悬而未决。
我们所称的“Baby M案”或许是最著名的涉及“代孕母亲(surrogate motherhood)”的案例,但在这个案例中使用“代孕母亲”这个词可能会产生误导。Mary Beth Whitehead同意用William Stern的精子受孕,并同意将所生下的孩子交给他和他的妻子,报酬为1万美元。然而,在生下孩子并将孩子交给William Stern 一家后,她感到非常痛苦。关于亲权的冲突爆发,新泽西州的法院最初将全部监护权交给了William夫妇,并忽视了Whitehead是孩子的基因母亲和分娩母亲的事实。上诉之后,判决被推翻,代孕合同被宣判无效。法院将监护权判给William夫妇,但同时判决Whitehead享有探视权。
女性主义者对商业代孕存在着很大分歧。支持代孕母亲的女性主义者的人经常强调代孕行为带来更大的自由。代孕合同让女性对她们的生育行为有额外的选择。Carmel Shalev(1989)则进一步主张,禁止这类合同意味着没有对女性所做的选择给予应有的尊重。如果一位女性自愿签订合同来生育孩子,阻止她的选择不仅是家长式的,而且还贬低了她的尊严。
商业代孕的支持者还严格区分代孕和买卖儿童:不是儿童作为商品来交易,而是女性的生育服务可以被出售。我们允许男性出售他们自己的精子,为什么要禁止女性参与类似的交易呢?最后,支持者强调,对男同性恋、女同性恋以及独身者来说,商业代孕是能够让他们成为父母的新途径。
批评商业代孕的人也提出了多种不同的反对意见。可能最常见的反对观点是,再生产劳动(reproductive labor)与其他劳动不同。Margaret Jane Radin (1988)和卡罗尔·帕特曼(1983) 强调孕育一个孩子的劳动方式与其他劳动相比起来,与“女性”身份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代孕合同涉及对自我的某些方面的异化,这种异化程度如此极端,以至于它被视为一种不合法的行为。与出售精子不同,怀孕是长期的、复杂的,还牵涉到母亲和胎儿之间情感和身体层面的联系。(参见Rich 1976从现象学角度对怀孕作的精彩分析。)
Elizabeth Anderson (1990)赞同这一反对意见,但她补充说,代孕合同也使妇女与她的孩子关系疏远,而且经常涉及剥削,因为代孕母亲更为贫困,比买方也更容易在情感上受伤。其他反对意见则强调代孕会使得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联系减弱,儿童会格外脆弱。
Satz(1992)认为,基于再生产劳动和我们自我之间的密切联系而提出反对存在局限性。作家与他们的写作紧密相连,但他们也希望借其小说获得报酬。此外,如果母亲和胎儿/再生产劳动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那么如何能为堕胎辩护呢?相反,Satz的论点强调了商业代孕的背景: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商业代孕使女性的劳动被他人利用、控制,并强化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例如,代孕合同赋予买家对女性身体的实质控制权,决定女性吃什么、喝什么和做什么;也可能加深女人是育儿机器这样的偏见。最后,代孕市场中的种族和阶级维度也需要考虑。在另一起著名的涉及商业代孕案件中,一名法官将一位非裔美国女性所生的孩子称为她所生孩子的“奶妈”(该孩子的基因来自白人父亲和菲律宾母亲),并拒绝赋予她任何探视孩子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对体外受精、商业代孕以及配子市场等的监管十分宽松,也有许多营利性机构参与了这些生殖方式。相比之下,对领养的监管则很严格:可能的父母必须接受面谈和家访,这些过程往往十分麻烦。这种区别对待值得我们反思,尤其是因为许多生殖技术在运用时会涉及脆弱的第三方(译者注:如代孕母亲、卵子捐赠者等)(Spar 2006)。


女性主义者就家庭和生育话题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内容,通过迫使主流政治哲学考虑家庭对社会正义的重要性,她们改变了这个领域。但女性主义者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就像组建家庭和生育孩子的实践一样。最后,这是两个需要更多关注的领域:
(1)提出“家庭并非私人领域”并不等同于完全否定隐私概念的价值,也不意味着无法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划清界限。为了促进性别正义,公共政策对私人选择的干预可以到什么程度?在面对性别不公与其他道德考量(例如宗教自由与结社自由)时,如何实现平衡?
(2)除了少数例外,很少有女性主义哲学家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来改变有关家庭的制度安排,或应对这些制度安排。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创造性的家庭政策,以削弱几个世纪以来的性别等级制度。我们还需要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已经尝试过的一些政策,如改革劳动力市场、离婚法律以及为贫困家庭及其子女构建安全网的政策。
翻译|王新瑶、何欣恬、田晶晶
校对|汪姝文




